
方远,资深报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济南市首批签约作家,济南日报报业集团舜网文学顾问,山东省散文学会特聘专家。著有长篇小说《大河入海流》《大船队》《坠落的天使》等五部,小说集《寻找情人》,中篇小说《神龟出没》《门缝儿里的爱情》等二十余部,多篇作品被报刊转载、连载,收入各种选本及年选。长篇小说《河与海》《大船队》先后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和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长篇报告文学《光明路上追梦人》入选山东省作协重点扶持作品。曾获第一届、第四届山东省泰山文艺奖,泉城文艺奖、梁斌小说奖、山东省对外传播奖、济南文学奖及济南市第六、九、十一届文艺精品工程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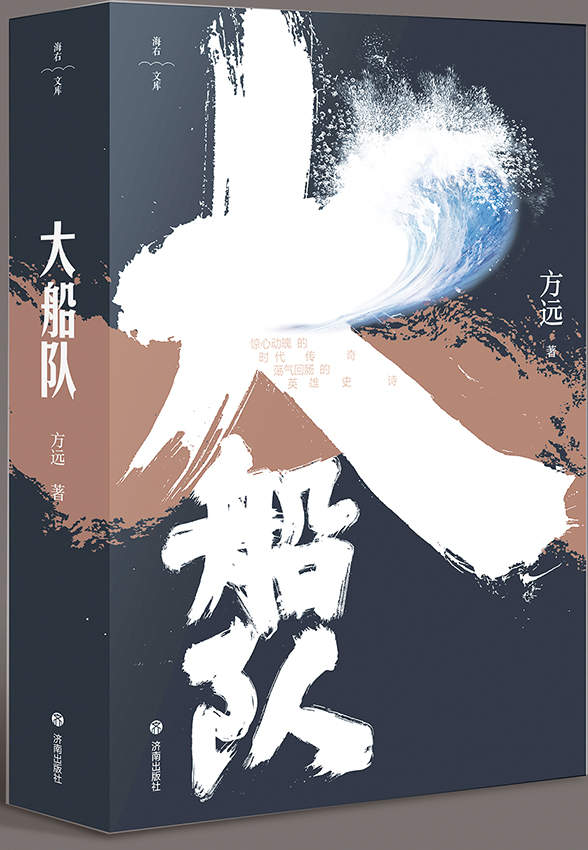

方远部分作品
日前,济南作家、泰山文艺奖获得者方远继长篇小说《大河入海流》之后,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大船队》,该书讲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宏德堂大船队离开莱州湾,带着振兴家族产业的梦想,穿越渤海湾,驶向东三省,开启海上运输业的故事。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风云和汪洋大海的惊涛骇浪中,大船队险象环生,历尽磨难。竞争对手的明枪暗箭,土匪海盗的杀人放火,日本鬼子的奸淫掳掠……每一桩生意都是一次短兵相接,每一次大海航行皆成为一次冒险之旅,而国难当头时的挺身而出与无畏牺牲则彰显了一个家族的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大船队的创建与消亡与四个女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也与国家的命运血肉相连。守旧与变革,仁慈与残暴,杀戮与拯救,正义与邪恶……两股势力的较量引出环环相扣的故事,既惊心动魄,又耐人寻味。
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先后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扶持项目、济南市“海右文学精品工程”、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和芒果TV“新芒文学计划”,是近年来我省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日前,记者就作品的创作过程、素材来源、主题呈现、人物刻画等问题采访了方远。
记者:祝贺您再次推出如此厚重的长篇作品。我注意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在推荐语中写道:“‘大船队’,这可能真的是不曾有人讲述的故事。在北方,一群农民向着大海,迎接新的、不确定的命运。他们将驾船穿越动荡的历史,他们成为民族秘史中的英雄。”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大海上穿梭的大船队虽已消失于时空深处,但作为“民族秘史”的组成部分,留在了您的这部作品中。在我们过去的交流中,我知道,“大船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那么,它如何引发了您写作的欲望,作品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您有过哪些取舍?
方远: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独特记忆,有荣耀,也有耻辱,有欢乐,也有痛苦。正是千千万万个不同的家族记忆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也就是所谓的“民族秘史”。我生在济南,却是在家乡莱州一个叫“过西”的村庄里长大的。那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母让我回乡陪伴年迈的祖母,从而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时代。乡村传说多,比方,我常常听到方氏家族八大堂的故事,自然包括我祖辈的同德堂。我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那时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以城市题材为主。我没有把目光投向我的家乡与方氏家族,是因为没有创作的冲动,当时并不知道,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已经埋藏在了我的记忆深处。直到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再次回到家乡,站在村后的王河大坝上,望着入海口的余晖,儿时的记忆莫名地被激活。于是,我在河与海交际处的氤氲云烟里,看到我的先人们身披霞光,迈着四方步,款款地向我走来。现在想想,这真是一个奇异的场景,如梦似幻,却真实地出现了。我突然意识到,是该将方氏家族的先人们写进我的作品了,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或者缅怀,而是一种责任,家族的和民族的。儿时听到的真实故事是不完整的,反而给了我更大的想象空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自由而肆意地行走,在现在与过去的情境中来回切换或布排,真实故事的取舍以及情节的虚构、设计基本是在下意识中完成的。顺其自然,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记者:您的创作起步很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很多中短篇小说发表在省内外各大文学杂志上,可否谈谈您的创作经历?
方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拿起笔来,开始学写小说。1985年,我的处女作《楼梯道上那盏灯》发表在《济南日报》“趵突”副刊上。这是一篇小小说,却像一盏灯一样照亮了我的文学创作之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我的中篇小说陆续发表在《钟山》《大家》《小说月报·原创版》等文学刊物上,有许多作品被《小说选刊》等报刊转载或连载,也有作品被收入年选和选本,还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但是,我的职业是记者,为了干好本职工作,我不得不放弃小说创作。那时,正好有一本小说集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在题为《爱心依旧》的序言里,我写了我的这种心情。告别是为了重逢,我如此写道。我相信,我还会再回来,继续我的文学之梦。十多年后,我真的回来了,却为此放弃了许多已经得到的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记者:在《大船队》之前,您还创作过一部长篇小说《大河入海流》,并第二次获得泰山文艺奖的长篇小说奖。这两部作品都均为海洋题材,海洋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两部长篇之间存在哪些内在关联?
方远:长在海边的人当然会热爱海洋,那是来自生命深处的情感。海洋比陆地更广阔,它既是温顺平和的,又是桀骜不驯的,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涌,为故事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宽阔的叙述平台。而从陆地走向海洋,更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仅从小说本身来说,海洋具有某种积极的、现代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大船队》是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大河入海流》的姊妹篇。《大船队》的一些内容原本是放在《大河入海流》里的,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由于篇幅过大,已超过七十余万,只好忍痛割爱,将《大船队》从中分离出来,形成单独的长篇。
记者:您的作品以故事见长,您善于讲述故事,营造矛盾冲突,复原历史场景,塑造典型人物,而且基本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读这部作品,“现场感”与“画面感”很强。您选择这样的书写方式,是否对现实主义情有独钟,还是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比如更便于拍成影视作品?
方远:小说家大多是会讲故事的人,一部小说好与不好,读者能否读得下去,读得进去,也算是一个评判标准吧。当然,小说是叙述的艺术,语言也是十分重要的,好的语言与好的故事相得益彰,典型人物便应运而生,现场感和画面感也就自然显现出来了。对每个小说初写者来说,总会先反复精读经典小说,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最早读的《红与黑》《包法利夫人》《战争与和平》等等,都是现实主义代表作。那么,自己写作的时候,觉得小说就应该这么写。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后来才知道的。先实践,后理论,这是我的创作途径,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属于意外之喜,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小说就是小说,能写好就满足了,我并无他求。
记者:如此磅礴的作品无疑是个浩大工程,您做了哪些前期准备,又如何破解了故事的复杂性所带来的叙述难度?请谈谈这部作品的构思与结构。
方远:每部小说的前期准备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首先是素材的积累与取舍,然后便是核准相应的专业知识,比方写《大船队》,故事可以虚构,时代背景、船的构造、地理特征、海洋特性、航海知识等等,这些要素则必须是有案可稽的,如果出现了纰漏,不仅会贻笑大方,在读者心中,你想让虚构的故事真实化的努力也会打了折扣,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某种程度上,构思与结构决定着小说的成败。我写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总是先有开头和结尾,如果我觉得开头和结尾够精彩了,就是有了所谓的“凤头”和“豹尾”,就开始动笔了。“猪肚”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丰满起来的,就像打开了水龙头,又知道水最终会流向哪里,那么,水的流动过程便是小说的“猪肚”。自然,水是不能让它直流的,要像黄河那样九曲十八弯,甚至要截断后再疏通,再截断,再疏通,眼看就要“奔流直下”了,就制造“事端”再拦下来,或者让它改道。如此往复,不厌其烦。“水流”是小说的主线,在它的折折弯弯里,便是铺垫和伏笔、倒叙和插叙、明线和暗线,等等。其实,小说的构思与结构不能墨守成规,是因人因作品而异的。我觉得,这样的构思与结构更能体现我的本意和创意,更能创作出好的小说来,我就理所当然地坚持下去。
记者:在这部作品中,您用十分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几位女性的生动形象,比如宋家宁、任明凡、范小娆等,这些女性虽然出身、经历不同,却各有各的痛苦与不幸。那么,您是如何怀着同情去解读塑造她们的形象的,又通过她们剖析了哪些造成这些痛苦与不幸的时代因素?
方远:在《大船队》的构思过程中,这三个女性人物是连同主要人物一起出现的。当然,她们都是配角,是为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服务的。三个女人一台戏,小说中怎么能没有女人呢?她们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女人是多为男人的附庸,有心甘情愿的,也有被逼无奈的,也可以说,有顺从的,也有反抗的。特定的年代造就了特定的女性人物,无论她们怎么挣扎,也逃不出那个时代的局限,经历痛苦与不幸。我并没有刻意用同情的语调去塑造她们的形象,甚至在写作过程中,这三个女性人物的最终命运与我当初构思时已大相径庭,原来活下来的最后死了,而原来死了的却反而活了下来。我是一个旁观者、叙述者,用冷静甚至冷漠的笔墨去叙说她们,还原特定年代的残酷现实。人都是有同情心的,这种同情是读者自己体会到的,或者说,读者认为,她们是值得同情的。当然,这也是我写作时的心态。
记者:您在作品中塑造了宏德堂主人方英典的正面形象,宏德堂之所以兴盛百年,靠的是秉持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您似乎更突出了他的大仁与大义,比如他的以德报怨、仗义疏财,收留并培养了前来投靠的年轻人以及三位苦命的女性。读之不禁感慨这样的仁心与德行才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具体体现,它不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亡。这样的人物在那个年代有没有原型?方英典这个人物身上似乎寄托了您的道德理想与家国情怀,塑造他,您动用了哪些家族记忆和生活阅历?
方远:先圣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我始终对君子怀有崇敬之心,对我而言,君子也是一种道德观念。现实中,我家族的堂号为“同德堂”,在小说中,我接受了父亲的建议,换了一个字,名为“宏德堂”。万变不离其宗,有一个“德”字就足够了。在《论语》里,关于“德”的内容甚多,仁爱、忠诚、知耻等等,这是君子的行为规范,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知道,先人们起的堂号绝不会是信手拈来的,名称决定了方氏家族的道德与价值趋向。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始终总有一个“德”字在萦绕,像神灵一样。方英典不是一个人,是方氏家族的综合体,甚至还有我父亲的影子。我“移花接木”,或者是“张冠李戴”,更或者是将诸多有德之人集于一体,塑造了方英典这个典型形象。
记者:《大船队》中,方英典是个核心人物,也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那么,您是如何思考与展现方英典复杂的人格内涵的?它的意义与价值何在?
方远:方英典这个人物必然带着旧时代的烙印与传统治家的保守思想,他是一个“矛盾体”,他一手破坏了儿子的婚姻却是出乎“信”,他收留刘小虎、宋家宁、范小娆是出乎“仁”,他以德报怨于宋占山是出乎“德”“忍”“智”,他对待同行是出乎“信”……当然,这些方面综合于他身上,使他成为一个复杂的存在,尽管他制造了儿子的悲剧,但他的抉择恰恰证明了他的方正人格与仁爱之心。我由此想到,即便优秀的文化在复杂的人生、人性面前也并不能输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但可以给人以抉择的基本准则,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生观或“内心的道德律”。抉择往往是痛苦的,但又是必须的。方英典在祠堂里烧毁了父亲立下的不能出海经商的遗嘱,并虔敬地告知列位祖先,他表现出的现代意识、开拓精神和雄心壮志是毋庸置疑的,他并非顽固的保守派,而是时代的先行者,其中也包含了现代中国从农业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隐喻。尽管他一言堂、说一不二,但深怀恻隐之心和刚正不阿的做人原则,证明他是位人格高大、格局阔大的儒商,从他购买武老汉的海草房与宋占山完全不同的取舍上就可见一斑,这样的例子很多。
小说写的就是人,人性。那么在小说中,我就写这一个人,他是复杂的,是有个性的,也是有正反两面的。《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本善。然而,我感受到,在现实社会里,善却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后修的,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在于是否修善,是否能遏制住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恶。换句话说,是否自律,是否有自我约束。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想想看,这样的君子标准是不是很苛刻?若想做到,是不是难上加难?君子“内心的道德律”既必须,也痛苦。所以,在小说里,方英典活得很难,很委屈,也很疲惫。方英典确实是一个矛盾体,他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那么,这个时期的社会和人就都是一个矛盾体,旧的、新的,开放的、保守的,先进的、落后的,就像四季变化中的风向,一会儿南风压过北风,一会儿北风又压过南风。但是,在风向的不断纠缠中,铁定的自然规律是不会被打破的。比方,春天要来了,北风再怎么拼命地反扑也挡不住春天的脚步,或许,这就叫大势所趋吧。方英典的成功正是由于他没有逆流而上,而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改变自己,也改变了宏德堂。但是,小说写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而这个过程很曲折,变与不变都非常艰难,是一种煎熬。比方说,他维护旧的传统与思想是一种潜意识,而他的现代观念与开拓精神却是他明智的觉醒与勇敢的抉择。道德与价值趋向是造就人格的重要因素,复杂的社会与复杂的人格血肉相连,方英典的人格魅力正是因为复杂而立体可信。
记者:中国传统社会阶层中的士、农、工、商,进入现代社会后必然被打破,旧时代的中国乡土必然会经历新兴社会思潮的涤荡,但那些植根深入的文化基因是不会被清除与消解的。您对百年家族史的深探往往给读者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比如“宏德堂”和主人公方英典的精神内核其实是“士”,所谓“以文传家,以德持家”;其家族的经营、发展和繁荣则源自和倚靠“农”与“商”,却绝非“熙来”“攘往”,为“利”而生、而存。因而,您并未在“挽歌”与“颂歌”之间作出判断与选择,只是呈现了一个时代的波澜壮阔与世道人心。我相信这其中除了有您对一个时代的基本判断外,也有对个体与家族、家族与传承、传承与历史、时代与社会的深层关系的探究,您的褒贬、认同与拒斥的态度是明晰的。那么,面对历史与文化,您认为一位成功的作家应该具备哪些素养去更本质地揭示真实与真相?
方远:小的时候,我读小说,常常这样感叹:作家怎么什么都懂啊?后来,我也写小说了,才知道,原来作家并不是什么都懂,而是什么都得学。不耻下问,不懂就学,没有领域的限制,要把自己的肚子当作一个杂货铺,什么都得往里面装。许多与文学无关的书,读的时候觉得没用,其实,以后肯定有大用场。伟大的作家肯定是伟大的哲学家,像托尔斯泰,像萨特。当然,作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要对世间万物都抱有好奇心,都感兴趣。我觉得,有了知识,有了阅历,有了哲学思想,才会将作家的想象力、发现力、感受力、洞察力、捕捉力、判断力等发挥到极致。作家的形象思维或许是一种天赋,而逻辑思维则是通过学习、观察、思考修炼得来的,而写小说,两者缺一不可。
记者:我认为您的《大船队》隐含着深沉的“乡愁”。所谓“乡愁”,其实关乎我们民族文化的根脉、气脉,关乎我们如何看待历史、思索当下、面向未来。您创作了两部可称之为“乡愁”之作的长篇小说,您对“乡愁”的理解包含并超越了故土与家族,更包括了崇高的文化信念,可否谈谈它的现实意义?我认为这同样是《大船队》的现实意义所在。我们今天讲“乡愁”,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其核心是什么?您觉得有哪些是应该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却是“边走边丢失”的?“宏德堂”作为您的书写样本,它的兴衰之变能给我们提供哪些思考?
方远:近几年来,“乡愁”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说明我们离乡村越来越远了。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怎么会忘记养育自己的家乡呢?想念家乡,又一时回不去,于是就得了思乡病,高雅的说法便是“乡愁”吧。人们会常常自问,我是谁?我从哪来?我要到哪去?这便是有趣的哲学三问。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家乡来,要到或者到了城市。这个质朴而幼稚的答案是不是可以解释为乡愁的诞生?其实,乡愁不愁,它是一种文化传承,延续着民族的历史与情感,是风筝的线,大树的根,是不能忘却的纪念。丢失的才觉得的珍贵,那么,对我这个离开家乡四十多年的人来说,乡愁便是一种忧伤的情绪,一种思念家乡的情感状态。我写《大河入海流》,写《大船队》,是为了向家乡致敬,也是为了我的乡愁有一个表述与宣泄的窗口,以抚慰我的心灵。乡村的兴衰,家族的兴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处在“兴”的时代,你是幸运的,你处在“衰”的时代,想必更幸运。这是因为,衰让你警醒,让你反思,让你有了改进的方向,总而言之,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记者:《大船队》塑造了各具性格的人物群像,通过他们复杂纠葛的关系以及命运发展的逻辑结构故事情节,并以此生动展现了家与国、时代与命运、个人与家族、传统与现代、革命与爱情、正义与邪恶、侵略与反抗所交织而成的波诡云谲的历史风云,您如何看待您笔下的人物与所处时代的关系,可否举例说明,比如江秀芝、罗良基、蔡铣朴等次要人物的刻画?
方远:江秀芝从一个小家碧玉到革命者,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是因为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遇到了引路人,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必然是因为她接受了新式的教育,思想开放,理想坚定,同时,她又是一个旧时代的受害者,那么,迟早有一天,她会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改变自己的不幸命运。在原来的构思中,罗良基这个人物是一坏到底的,写到一半,我却改变了初衷。蔡铣朴是个中性人物,或者说,我是想根据故事的发展再决定他会走向哪一面。时代与人物成长密不可分,在我编织的故事中,罗良基和蔡铣朴都因为外部因素发生了转变。
记者:您在作品中写到了很多过去的风情风物,比如饮食文化、婚丧嫁娶等等风俗,这些作为必要的叙事补充让作品更富张力、更加饱满,这些经验从何而来?
方远:经验来自于个人的阅历,也来自于地方史志。从写《大河入海流》起,我就搜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从而更深入地了解莱州的风土人情。地方风俗是故事真实性很重要的证明,在写作中,每当有重大的事件发生,我总会想方设法地与地方风俗结合起来,既描述了独特的风俗,也对故事的发展起到良好的烘托作用。
记者:您的父亲方肇瑞先生是这部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作为获得过两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飞天奖”的剧作家,他对您创作的这部作品有没有具体的帮助和指导意见,或许很多故事都是他讲给您听的,对此,您又做过哪些组合、拼接和改造?
方远:很多朋友说,我的写作来自于父亲的遗传基因,这一点我是认可的。父亲是一位剧作家,我从小在家里听他与同事们讨论剧本,也就是听他们讲故事。记得有一次,他们在讨论爱情故事,有情节,也有细节,无意中发现我这个偷听者,就把我撵走了。我善于编故事,或许这就是启蒙。小说中的很多故事肯定是父亲讲给我的,他是“同德堂”末期的当事者之一。有的故事离现在很近,父亲经历过;有的故事离现在很远,父亲也是听长辈讲述的。文学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有的故事我都没有根据发生的时间来讲述,而是根据小说内核的需要,就像您讲的,重新组合、拼接、改造,使每个故事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大河入海流》和《大船队》,我的父亲都是第一读者。他从不干预我的构思和写作,在我写完每一章节,我会打印出来,请父亲审阅。他非常尊重我的想法,不对人物或故事提出大的改动,只是对某些情节或者细节提出建议,比方说,这个故事在这里还要渲染一下,如果这样写是不是会更好?这个人物死得太不值了,对不起前面的铺垫等等。当然,在我风风火火地度过了半辈子之后,我回归文学,是他老人家最为高兴的事。
记者:请谈谈您未来的创作计划。
方远:近十年来,我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两部长篇报告文学,近二百万字,收获不大也不小。我正在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写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大学毕业的这一代人的奋斗史、成长史、心灵史。各色人物在一个个地往外蹦,拦都拦不住。都是自己经历过的事,都是自己接触过的人,想想就很有趣。自然,我也有信心把它写好。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