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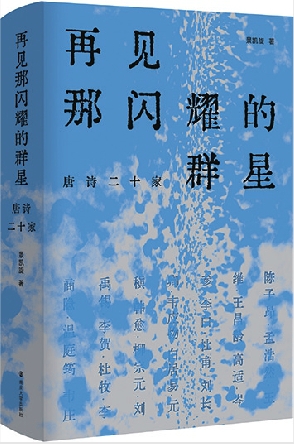
当我们在背诵唐诗的时候,我们在想些什么?或许诗歌中那浩瀚美好的意境早已让我们迷醉,但其实,腾出一点思维的空间,遥望唐诗的天空,我们或许会别有一番发现。
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景凯旋先生新著《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以下简称《唐诗二十家》),就是这样一部别有新见的诗歌随笔集。这不是一部研究唐诗的专著,而是作者在唐诗中的一次漫长游历。20位诗人,每一位都有独特的阐释角度,难得的是,作者不仅试图在唐诗的背后寻绎诗人的观念与价值,还时常将其放置在整个人类文明的星空之下进行观照。于是,在这个特别艰难的时期,“重读唐诗,或许会有一种更深切的感受”。
通过诗歌,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
景凯旋以为,将诗歌比喻为天上的星辰并不算夸张,先民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常常仰望星空,寻找生活的答案。“《诗经》中就有许多描写星辰的诗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今天读《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仍能感受到先民丰富的情感世界。中华民族是一个感性的民族,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就是诗歌。在诗歌中,古人诉说自己的情怀,表达人生的悲欢离合,甚至追问宇宙的秩序。”
在《唐诗二十家》一书的序中,景凯旋写道,现代人总是感叹再也不会出现唐诗那样的高峰了,这是因为唐代恰好处于一个长时段历史的转折期。“唐人的思维意识已然处于自然与历史之间,前者促成了盛唐诗的浑然天成,后者使中晚唐诗转向了世俗与自我。唐代诗人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最有利于诗歌创作的时期,个体意识的发育逐渐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诗人们有了更多的创造空间,可以运用各种形式,表现不同题材。”
另外,景凯旋认为,诗歌在唐代占有崇高的地位,帝王的喜好和科举的实行功不可没,“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包括帝王、将相、布衣、妇女、僧人、道士等,都喜欢写诗。可以说,诗歌创作是唐代文人的事业,士大夫阶层几乎都是文学之士,他们深信诗人在历史上的声誉将高过帝王,他们为自己的内心而写,希望自己的诗能流传后世。对于他们,诗歌不仅是生活的反映,更是生活的扩张。”
唐代诗人的精神是向外的,视野是壮阔的,唐代的确是一个思想开放的朝代。景凯旋在序言中写道,“他们的宗教生活是平和的,世俗生活是热情的。士人出入魏阙与江湖之间,用儒家的‘兼济’追求人生的成功,用佛教的‘无执’获得失意的解脱。这种儒道互补的矛盾思维对于他们似乎没有任何违和感,总能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刻抽身而去。可以说,诗歌已经渗透到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诗歌,我们可以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从中寻觅到自己的知音。”
而除了人生的体悟,农耕时代的人对于自然的感受,显然也要比今人更加丰富细腻。“毫无疑问,人存在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人本身,但现代的事实是,外在的物理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已经完全分裂,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人们追求活着的幸福,相信人死后一切都不会留存,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失去了对自然的想象力和审美力,再也听不懂飞鸟的呢喃和草虫的鸣声。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学会与自然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正如美国诗人乔丽·格雷厄姆所说,诗歌是匆忙生活的中断和暂停,它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日益碎片化的时代,重新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
艺术的感受力与生命的厚度
以诗歌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自然要在细致分析每一位诗人主要作品和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窥见诗人的艺术观、价值观,并由此探求诗人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作者以为,就诗歌所呈现的生命样式而言,王维渴望归去,李白憧憬远方,杜甫则始终行走在路上。但难得的是,书中并非只有如此简单的概括,而是有抽丝剥茧的分析,甚至有中西价值观的对比。
比如说起王维,谁都会想到“山水诗人”“山水画家”这样的身份标签。在《唐诗二十家》中,作者拈出“山中习静观朝槿”为题,起笔先迅速勾勒出一个“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高人”形象。“纵观有唐一代诗人,生前就称名于世者不少,但由皇帝下诏搜集诗歌,并许以‘天下文宗’之美誉,这样的优遇却很罕见。代宗的诏书实际上代表了一种钦定的诗歌标准,那就是王维诗歌的两大类型:应制与隐逸。”而隐逸之风和佛教的兴盛有关。作者认为,在王维的诗中,经常出现“性空”“心空”“无染”“无生”等佛教术语,宣扬佛教的性空缘起,而“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正是不执一端的中道观。从早年的“相逢意气为君饮”的豪迈到晚年“渔歌入浦深”的禅悟,王维完成了一个佛教徒的觉悟过程。“禅悟的自由是放弃的自由,无论是谈笑终日,还是渔歌入浦,都是在突出一种随缘自在的心情。”然而,作者认为,诗歌如果仅仅是阐明无执的禅理,终究会显得过于冷淡。“佛教的无欲在观照外物时类似于康德的‘美的无功利性’,因而能从静观直觉到自然的优美,却不能产生崇高感。按照康德的观点,崇高是在对象的无形式中发现的,它只发生在观念里,关涉人性深处的伦理内容。”
由此,作者认为,王维的诗“是一种知性的美,不是一种伦理的美”,“他的归去没有远方的参照,因而他的诗缺少内在的人性冲突,缺乏附着于自由而不是自然的情感,总是引导读者进入无我的境界,让人沉静下去。恰如顾随先生所说:‘右丞高处到佛,而坏在无黑白,无痛痒。’对佛教来说,人生的痛苦就是因为太过于执着于生活表象,而不能认识到万物皆空的本质,所以需要通过无执的智慧来远离痛苦,并将这种智慧视作自由的获得,从而形成中国诗歌的一大特点——归去。”
作者认为,在西方读者眼里,王维这类超脱的诗被视作中国诗歌的主要特征,这使得西方人对东方诗歌产生了一个并不完全准确的印象,“用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话说,诗人对于把分配给个人生命的时间与全人类的时间联系起来的一切事物漠不关心。王维的诗就是如此,他是中国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在他的诗中,对于存在意义的寻求总是止于空无,‘归去’于是成为他对人生的一种妥协和回避。”在这一个意义上,作者认为,王维“是一个有很高感受力的画家,但绝不是一个有生命厚度的诗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更为推崇杜甫,“他乡复行役”,这就是杜甫的人生概括,作者认为,纯粹的远方与归去都已褪去理想的色彩,诗意的栖居就在此处,在当下,在实际的人生中,那是对人类真实生活的深切理解。“因此,不同于王维的当下,杜甫的当下连着远方;也不同于李白的自然,杜甫的自然中沉淀着历史。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中,只有少数几个诗人能够一直活在后世人的心中,而杜甫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正是杜甫给生活的日常性赋予了永恒和普遍的意义,将实际人生提升到崇高的境界。”
在山水中宣泄自己的孤愤
这样中西文化观照下的唐诗解读,无疑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诗人及其时代的精神。它因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坐标,让我们对时时仰望的群星璀璨的唐诗天空,有了更加宽广的理解。即便对于诗仙李白,即便对于那首家喻户晓的《望庐山瀑布》,作者也找来一首18世纪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来对比。歌德的这首《水上精灵之歌》也以瀑布为象喻,在诗中将飞流想象成人生的过程:“人的灵魂/像是水。/它来自天空,/它升上天空,/它必须又/降落地上,/它永远循环。”作者认为,“歌德诗中既有世俗的情感,又有超越的境界。李白的诗缺乏这样的永恒性与人间性,他的诗中没有人,他那种道教徒的观念中既没有彼岸世界,又拒绝完全融入人世,因而始终与他人和外界保持着一种内在的紧张。”
李白诗歌的意义当然是巨大的,作者认为,与汉魏咏史诗、唐代怀古诗中的历史时间相比,李白的怀古诗很少具有历史或现实的价值判断,他的时间意识属于更加永恒的自然时间。“李白诗歌的真正价值其实正在这里。及时行乐对他而言不是怀才不遇的排解,而是对生命终极关怀的苦恼。他时时刻刻都在与生命之短暂作斗争,尽管浮生若梦,仍有‘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的慰藉。还是将生命托付给永恒的自然与诗歌吧。说到底,诗歌可以赋予人类这样的幻觉:我们能够有意义地活着。”
或许无法用先进还是落后来评判,但坐标系的扩大无疑让我们看到面对唐诗时不同的眼光。面对同样的夕阳,李商隐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歌德说:“西沉的永远是这同一个太阳。”李商隐感受到的是当下时间的短暂,歌德体验到的是超越时间的永恒。这似乎代表了中西文化在宇宙意识上的某种差异。从诗中寻找这种差异,是一条经由诗而窥见历史的独特路径,如景凯旋所言,“中国士人不是没有自由意识,但这种意识并未见于反抗的姿态——就像19世纪流放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知识人那样,而是见于流放边陲蛮荒之地的痛苦与绝望。在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中国文化终究没能从自我欲求的实现中发展出个人自由的观念,没能从天人之际的思考中产生出自然权利的思想,进而找到一种更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因而诗人对于自由的意识,就只能是在山水中宣泄自己的孤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