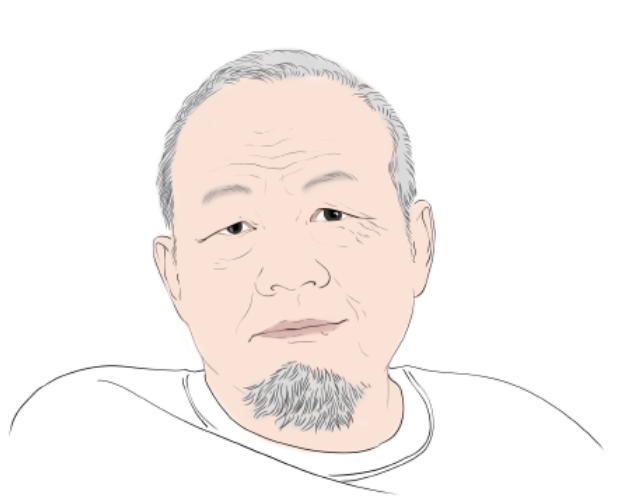
孙婷婷 绘
“天空如漏斗。掉下来了鲲鹏志。”
一首诗是整体情感和思想的律动,因此“佳句摘抄”并非读诗之道,但是当诗人孙文波朗诵起他的《C小调》,这句诗还是如此强烈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今年6月底于章丘明水古城举行的首届清照诗歌节的诗歌朗诵会上,舞台背后古意盎然的老房子是朗诵会的背景,诗人们在流光溢彩的灯光下读自己的诗。与众不同的是,孙文波用四川话朗声诵读,格外有一种浑厚婉转的力量。
这位已经68岁的诗人,老骥伏枥,依然有着一腔诗歌的“鲲鹏志”,依然在个体与世界的连接中探索现代诗的“诗意完成”,并期待在诗歌存在的意义上有所建设。作为中国少有的几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诗,至今仍然保持旺盛创作力的实力诗人之一,孙文波的诗歌之路从未停息。
写诗,成为“另一个人”
“每一个写诗的人最初的写作动机都大同小异,那就是对阅读的热爱。促成我提笔写第一首诗的原因也大抵如此。”
孙文波是四川成都人,1956年出生。时代使然,他很早就下乡当了知青,又在下乡的地方去当了兵。退伍后回到成都,进了一家工厂当了工人。那时候孙文波的阅读面已经很广,梦想着以后当个小说家。有一次工厂的同事组织诗歌朗诵会,因为看到他经常在午休时拿着一本书去茶馆看,就向他发出邀请,还让他“也写上两首”。回家之后孙文波就写了两首,而且在朗诵会上获得了年轻大学生的赞赏。这让孙文波觉得写诗并不困难,于是一发不可收。
而那个时代的诗歌氛围也让孙文波获益良多。置身于诗人群体让青春的诗心持续涌动,“朋友间的具体交流、互相激励非常有效。并不仅仅是称赞,你身边有写诗的朋友本身就是一种激励,你们会互相探讨,甚至比学赶超。”
事实上,写诗也彻底改变了孙文波的生活,让他成为“另一个人”。“如果不是写诗,我不会是现在的孙文波。”在和诗人哑石进行的一次对谈中,孙文波说:“我一直觉得诗歌是人生梦想的产物,具有改变人对生活看法的功能。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正是在写了几年诗,一些作品得到发表后,开始不满足一直待在工厂里便辞了职,全身心都投到与诗歌有关的生活中。如果不是因为写诗,我很可能早就是下岗工人,拿着微薄的退休金,不是无聊地在茶馆里与人穷侃,就是与人在苍蝇馆里喝酒。但诗歌却引领我走上另一种人生。不是因为写诗,我会去欧洲参加诗歌节,并游逛了像巴黎、布鲁塞尔、柏林这样的欧洲名城吗?不是因为写诗,我会去日本等地,获得一睹异域风光的机会吗?肯定不可能。如今我与之交往的朋友,大多是诗人,我们平时见面谈论的大多亦是与诗歌有关的话题。……总之一句话,诗歌不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还塑造了我们的人生。”
对孙文波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诗成为一种“能够培养人的孤独感的力量”,“它会使人建立起内心的强大。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过诗,让人在应对生命的厄难、变故时,能够变得从容、镇定,处理起来更加自如(虽然仍然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作为个体处理不了的)。所以如今回想起来,我对诗歌是充满感激之情的,我觉得正是与诗歌的结缘使我有了现在被确定的人生样态”。
“真实是诗意的”
在孙文波眼里,诗学观念的日渐清晰和成熟,当然伴随着阅读和写作的持续深入,伴随着对诗歌历史和生存处境的深入思考、辨析。“20世纪80年代,对我冲击和影响最大的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叶芝、艾略特、庞德、米沃什等等,他们引发了我对精神生活和文学的生成方式的持续思考,我突然发现,原来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谈论诗歌。”
孙文波至今非常认同艾略特在一篇诗学文论中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过了二十五岁后还想继续写作,特别是写诗,需要具备历史的意识。这种意识对于继续创作是几乎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不仅包括理解过去的过去性,即认识到历史事件的发生和时间的流逝,更重要的是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即认识到历史对我们的影响和历史遗产的价值。只有通过深入理解和吸收历史,作家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出更深的文化和情感内涵,从而使作品具有持久的魅力。”
孙文波说,一个诗人对诗歌发展脉络的深入了解,并非是对前人简单的模仿,而是要以此来思考什么才是写作真正的有效性,如何才能呈现人的生存处境,“写一种具有有效性的诗歌,是一个重要原则。对于我来说,你要写出你在你所生活的时代中体会到的思想的有效性、生命的有效性。你要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生活的反映,要对得起你生活的时代”。
由此,孙文波的诗歌原则极为清晰,那就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都要“坚持个人的、灵魂的真实”,因为“真实是诗意的”。
当然,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语言诗意”的获得才是抵达“真实诗意”的关键。孙文波一直有一个关于文学常量和变量的看法,“如果说托尔斯泰作品中体现的爱和死亡也是诗歌永恒的主题,是常量,中国古典文学对时间和风景关系的处理也是常量,那么追求语言的发展则是变量。‘五四’的白话文和古典的语言当然不同,如今我们的语言又和‘五四’时期有所不同。就像总有喜欢古典音乐的人在抵制现代音乐,很多古典文学的爱好者也看不上白话文。但我们其实可以既喜欢古典也喜欢现代。它们各有所长,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伟大成就。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保持一种发展的态度,是在不断生成、变化的纷繁复杂的语言中理解并捕捉到那些能有效生成你诗歌的意象、节奏和意义的语言”。
“新的出发”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不能在对传统的认识上找到它对今天的人类生活的帮助,不能增强我们认识现实的能力,那么,就是再怎么夸夸其谈地讲传统,也是没有意义的”。孙文波认为,“真”的基础,就是对现实复杂性的时刻认知,而一个当代诗人,有责任在诗歌中将其“清晰地”呈现出来。在2020年出版的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的“后记”中,孙文波这样写道:“在当代的诗歌环境中,简单主义流行,很多人把诗的复杂性看作不可取的弊病。这与我的认识刚好相反。我认为,对语言复杂性的追寻,正是文学当代性的一大要求。面对着变得越来越混乱的人类处境,如果不能以更为复杂的方法来处理现实带给人类的困惑,诗便很难完成对我们置身其间的世界的解析。寻找呈现复杂性的方法,恰恰是我们作为诗人的责任。只是我并不想人们在看到复杂性在诗中出现,便认为它是不清晰的。语言的复杂性与叙述的清晰是两个方面的存在。正是由于此,在写作中我更加努力想做到的是,让这部诗有一种清晰的面貌——对个人经验复杂化的处理,带来的是清楚地阐释了当代生活带给人的变化多端的感受。”
在孙文波看来,一个成熟的诗人,越到后来,就越应该有一个坚硬的面对自我和世界的价值观,“时代对写作者的制约当然存在,唐代最杰出的诗人身上也能看到时代的束缚,我们只能保证我们在诗歌中传递的真,是诚恳的发自内心的,是能尽量靠近真理的”。
随着自己诗学观念的日益成熟,或许很难再让他人影响自己,但杜甫的影响持续不断,“不是因为他的古典诗的写作,而是因为他对待文学和生命的态度,因为他坚定的文学信念,因为他不断进步的写作姿态。他是少有的越到晚年写得越好的诗人。”
在与诗人哑石的对谈中,孙文波谈到了晚年写作,他认为,晚年写作,也是一种“重新开始的新的写作”,是“一次新的出发”,“晚年写作更复杂的要求在于,怎么做到在写作中掌握剔除的技艺,即在写作中能够真正做到不单是对曾经的写作技艺的放弃,还要求从放弃中另外寻找到新的技艺。这样一来,如果真要我对晚年写作说上点什么的话,我想说的是:除了需要我们保持住诗所必须保留的激情、天真,进入晚年写作时的写作者,应该回到的是写作的幼稚状态,把每一首诗的产生都看作对过往写作的反对和矫正。我的确愿意把晚年写作看作是一个人反对自己的过去。至于一般人说的到了晚年,人应该学会澄明、清澈、简单地构建诗篇,这是对的。但我们也需要搞清楚什么是诗的澄明、清澈和简单。我认为只有做到使综合能力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以后,上面提到的那些才可以谈。”
【人物档案】
孙文波,1956年出生,四川成都人。1985年开始诗歌写作。作品被收入《后朦胧诗全集》《中国二十世纪新诗大典》《百年诗选》等多种选本。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瑞典语等。曾参与主编《中国诗歌评论》《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主编《当代诗》。著有诗集《地图上的旅行》《给小蓓的俪歌》《孙文波的诗》《与无关有关》《新山水诗》《洞背夜宴》《长途汽车上的笔记》等多部,文论集《在相对性中写作》《洞背笔记》。









